核心提示:因为在西安市委宣传部兼职,他们给我发了一个工作证,我拿着这个工作证到哪里都可以去调查。我就拿着这个工作证去采访各个地方,回来给《华商报》写深度报道,一写写好几个版。
“报业混蛋”:孤客张弓惊鹊燕
张弓惊,1971年出生。英语言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职研究生。现居北京。
曾供职于陕西华商报集团。任该集团所属的《华商报》(西安)、《新文化报》(长春)、《华商晨报》(沈阳)新闻中心主任、总编辑助理等职。
2001年主持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信息时报》(日报)的成功改版,任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
| |||||||||||||||||||||||||||
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公益时报》总编辑。
2002年5月至2003年9月,任中国中信集团(北京)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中信传媒集团)报业投资规划组组长。
2003年至2004年任厦门元通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并任《生活新报》(昆明)执行社长。
2004年到2005年参与创建清华紫光集团紫光传媒有限公司,任紫光传媒公司投资委员会副主任。
2005年9月入股内蒙古太阳晨光传媒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兼《内蒙古晨报》执行社长。并与投资伙伴一起参与北京等地多家传媒项目的投资。
赚钱,是支撑我选择这份职业的重要原因
六月的午后,空气有些燥热,似乎在酝酿一场雨。西安市的一所中学里刚刚结束了一个全体教师会议,会议主题是参加工作满一年的新教师转正的问题。会议刚刚结束,一个激动的男青年(也就是当年的我)闯入了校长办公室,冲到校长面前大声质问:“为什么不给我转正?”
校长是一位50多岁的女同志,她平静地看着我说:“你不是要调走吗?”
我愣了一下,心想她是从哪听说的?心里的愤怒并未平息,我继续说:“是不是我现在写调动申请,你就给我批?”
“行,你写我就批。”
盛怒的我匆匆走出校长室,一位老师追上来对我说:“校长已经给你办转正了,她只是吓唬你,想让你以后好好工作。你怎么还当真了?你别这样,我知道你刚到西安工作人生地不熟,你看你调到哪里去?”
“不行,我就要调走!”
我首先给《童话世界》编辑部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在大学时候就喜欢儿童文学,并写过几部连载童话(有一部还在地方的儿童节目里连续播放过),当时还任该杂志的总策划;该杂志的某位领导曾经认真地跟我谈过调我过去的事情。那边的负责人说:“年轻人你怎么这么着急啊?是不是稍微等一下啊?我们这边好几个人安排不过来啊……”
第二个电话,我打给了《华商报》。当时《华商报》的老总李涛听完只说了一句话:“行,你赶紧写申请吧,就来我们这里。”
那是1995年的夏天,我24岁。在此之前,我是西安44中一名不太称职的英语老师,在此之后,我走上了职业报人的道路。
如果再往前追溯,选择这个职业也许是注定的。
在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喜欢写东西,当时主要是特别爱诗歌,也写散文之类。那时候文学热,我发表一个小豆腐块赚几块钱,这对于来自农村生活拮据的我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赚钱,一直是支撑我选择这份职业的重要原因。有人说做新闻是为了理想,这种东西当然有,但鼓励我有勇气一直做下去的,还是赚钱。连我爱人都说我,骨子里是很俗气的。猎头.
没办法,小时候的经历就决定了我注定是要走市场化道路的。从前我们家的生活非常艰辛,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年年有人生病住院,一家人永远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
到了大学,我除了自己的专业英语还在好好学之外,其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赚钱上。那时写文章赚稿费,比当家教赚钱更容易。别人做家教一个月能赚几十块钱,我写文章一个月就能赚到一两百块钱。当时《当代青年》的固定栏目每期都用我的稿子;稿费比较高的《女友》杂志也曾经登过我的稿子。
大学毕业后,我和我爱人(也就是当时的女朋友)被分配到西安中学里当老师,但是需要交6000块钱的“进城费”。此时我上学时赚的钱都折腾完了,这6000块钱全是借的。我刚毕业一个月工资才280元,我和爱人商量,等还完这些钱再结婚。
那一年,我一个人干了八份工作,其中就包括在西安市委宣传部机关杂志《西安宣传》做编辑,以及做《华商报》的特约记者。
因为在西安市委宣传部兼职,他们给我发了一个工作证,我拿着这个工作证到哪里都可以去调查。我就拿着这个工作证去采访各个地方,回来给《华商报》写深度报道,一写写好几个版。
急着挣钱啊。我的兼职几乎囊括了所有我能够找到的挣钱的职位。不到一年,6000块钱全部还完了,但我的教师工作却走到了尽头。我知道不能怪校长,我的确是个不称职的老师,这一年从没给学生好好批改过作业。也许从另一个角度,她的确是想成全我;客观上也确实成全了我。
当我把调动申请拿到教育局的时候,教育局又让交三千块钱,我又打电话给《华商报》,李涛什么也没说,直接从他私人的钱包给我拿了钱。
如果说我的传媒从业经历要感谢什么人,第一个就是李涛,因为是他,把我从学校“买”出去了。
西安?北京?沈阳:亲历《华商报》的转型和腾飞
到了《华商报》,我着手组建记者部,招了好多记者,直接做了主任。直到现在,《华商报》好多干部都是我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当时一些记者最初连新闻是什么都不知道,几乎要我手把手地教。
在《华商报》,我精力充沛,喜欢干活,当时《华商报》一个星期出四个版,有三个版的内容是我自己采写的;我脾气不好,如果弄的东西不好我就爱骂人,别人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我性格比较野,跟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交往比较多,甚至因为搞社会新闻跟公检法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哥们。实际上,我也觉得奇怪,我这些年脾气并没有变好,但是一路走来却一直没有缺过朋友。
当时《华商报》出了一点特别的状况,总编李涛也被停职了。此时的《华商报》群龙无首,大家人心比较浮动。我跟编辑部主任老搞不到一块去,矛盾激烈的时候,我曾当着副社长的面一脚把编辑部主任从总编室里踹出去了……在《华商报》内忧外患的当口,我被当时的社长李大灿安排来北京创办《华商报》北京记者站。我就这样来了北京,住在了北京安定门外的京宝花园,地坛西门的正对面。现在有时候路过那里,还是特别亲。
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但是,因为是属于被“流放”,我根本没有心思跟这个祖国的心脏、古老的文化中心亲近。猎头公司.我一到北京,就一头扎进了采访中,既然是《华商报》,那就多做经济的稿子。我因为几个同学在北京,就通过他们介绍,接触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当时好像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都是从陕西出来的,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军扩、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人民大学的李义平、当时国资委研究中心的魏杰等等,我打听到地址电话,直接骑着自行车就去了。从安定门骑自行车到北大,我一路不带喘口气。认真采访,然后回来就熬夜写稿子,都是“大篇幅”。还有就是请这些教授们的一些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到记者站开研讨会。我把《华商报》北京记者站简直办成了一个财经俱乐部了。
现在想想,实际上那时我就跟那些经济学家在一起聊西部大开发的话题,比中央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提出都早;也聊企业上市等一些很专业的问题。记得当时与宋国青在北大三角地的食堂,一边喝啤酒一边聊“游资问题”,还争得脸红脖子粗。当时我实际上不懂经济,但经济学家懂。有一次采访香港来的一个人,他讲买壳上市,我就写买壳上市,回去以后《华商报》头版发了,甚至惊动了证监会的人打电话给华商报,要求报材料过去。
本来北京搞记者站,是作为华商集团在北京的公关办事处,也没指望写稿子。我写了稿子,社长兼华圣集团的董事长李大灿就让我把文章直接传给他的秘书,结果我每周几乎都会把他的传真纸都用光了。
当时我一个外交部工作的同学跟我说互联网好,我就弄了一台电脑,学习上网。DOS状态下进入NETSCAPE系统。当时的互联网上中文材料不多,有很多英文的财经类的信息。我恰好本科学的是英文。所以,除了那些采写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我还不断地给《华商报》发互联网上的经济信息。结果《华商报》几乎成了北京版了,从头到尾都是北京站传过去的消息。
我来北京快三个月的时候,我接到了社长的电话。那时社长要到长春办事,在北京转机,他让我去飞机场见他,说有几句话要跟我说。我跟社长在机场的停车场里见面了,我们坐在车里,他跟我说:“张弓惊,你这几个月干得好!《三秦都市报》有一个人叫张富汉,我想请他到咱们报社来。他现在要去成都见席文举,我明天也过去。你今天先去成都,跟张富汉见见,聊一聊。”我问:“我要不要先回西安?”他说:“你不要回西安,直接去成都吧!”我没来得及回去北京的住所,直接坐上飞机到了成都,见了张富汉和席文举。
那次的成都之行改变了《华商报》的命运。我们参观了《华西都市报》,也和张聊得很投机,我对他的想法也比较认同。张之所以请李大灿社长到成都,是因为他就想让大灿知道,我们《华商报》要做就做成《华西都市报》那样的报纸。第二天,社长到了。也就是那次成都之行,让李大灿终于下定决心,让张富汉到《华商报》任总编辑,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全面主持工作。《华商报》的腾飞也就从这次成都之行开始。
而我,就这样直接从成都回到西安。直到《华商报》在张富汉的领导下改版后半年,我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取行李。结果,我的行李早就被丢的不知去向了。我存在安定门地铁站的自行车,也找不见了……
在《华商报》报系里,我的最高职位是总编助理。记得那次在成都的时候,我偶然给张富汉讲互联网,《华西都市报》正好也有互联网。张就对我说:“互联网这么好,回去咱们也搞!”结果,一回西安,张让我做了新闻信息中心主任。
那时的《华商报》除了记者采访的新闻,其他新闻就都在我这儿出。广告猎头.一期八个版,有五个版是从我们部门出来的。这确实能锻炼人,现在《华商报》的很多干部都是出于我的部门。我这人比较喜欢揽事,一揽揽一堆,然后张富汉就把它一个个剥开。
张富汉说我的能量比较大,因为我干啥就一门心思想干好;不懂就学,就琢磨。我甚至当了一阵子《华商报》技术部的主任。现在《华商报》的域名还是我当时申请的,包括《华商报》早期那套基于互联网的发行软件都是在我的主持下做成的。当时《华商报》的发行系统各个站就能联网,底下订一份报纸总部即时就能看见。后来沈阳和长春那个系统也都是我做的。
后来我们部门分出来成为五六个部门:国内部、国际部、技术部、特稿部,还有法律协调小组,其他部门收不进去的,全放我这儿了。
实际上,进入报业,我最感激的人就是张富汉。应该说,是张富汉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报纸。而且,越到现在我越明白,《华商报》的成功不仅是作为报业在技术上的成功,更多的是作为企业运作上的成功;说到底,实际上也是张富汉做人的成功。有很多的报纸,在报纸的新闻运作、发行运作、广告运作上都比较优秀甚至比《华商报》更优秀,但是都没有达到《华商报》现在一样的成功,我认为就是因为在企业运作上不如《华商报》的缘故。
所以如果我的一生能够在这个行业有什么成就的话,首先应该感谢的人就是张富汉。他不仅领我进入了真正的市场化报业的门,更让我知道了,一个成熟的企业,应该怎么成熟地对待所处的市场和行政的环境;作为一个想做点事情的人,应该怎样成熟地对待所处的各种艰难和荣誉。
就在大家都干得不错的时候,《华商报》又出了一件事情,一篇报道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正好出在我们部门。
实际上那个稿子根本不是我发的,正好周末我休假,回老家去了。记者是我派出去采访的,但是发稿子却基本不关我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第一次的事情,比如接受有关机构的讯问、在笔录上面按指印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查,调查我的短暂的人生历史,调查我与个别敏感的历史事件和组织有没有关系等等……那时候我觉得恐怖极了,但是跟家里人也不敢说,怕父母担心,怕爱人上火,那时候小孩刚一岁,我就一个人忍受这种痛苦。
处理的结果就是:大年初一,老张给我打电话说:“张弓惊,是这样,咱们在沈阳要办一张报纸,你去沈阳吧!”
我就这样到了沈阳的《华商晨报》去了。老婆孩子在西安,我孤身一人过去,一去就是一年。当时我做总编辑助理,主管采访;抓采编当然也不松劲。天天比照几家竞争对手的报纸。他这个头条,我这个头条,我一定要比他强。搞“有奖新闻热线”,并天天把昨天谁提供线索并奖了多少钱的表格在头版登载。结果,有些事件,现场我们比警察都去得早;因为群众看到突发事件,往往先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再打110,因为我们有奖励嘛。
然后就是搞活动,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纪念,图书馆搞展览,征集纪念品。甚至主办电影首映式;张艺谋的电影《幸福时光》首映式就是《华商晨报》主办的。中央电视台曾经都专门报道我们主办的一些活动。
还有,我和发行部主任杨凡青关系好,我也很爱钻研,爱揽事,就开始掺和发行的事情。策划召开发行大会,亲笔给发行部主任起草极富煽动性的发言稿,洋洋一万言,一个通宵写完,会场上杨凡青念起来简直像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开发行大会发奖,最多的时候五千人卖报人员开会,大会上奖摩托车,发行状元奖一万块钱,当时得奖的人领到大奖激动得都哭了……“黄马甲”一下子在沈阳搞成了一场“黄色风暴”,刚创刊4个月,期发行量已经40万左右了。
广州?深圳?昆明?北京?内蒙古:开始从投资商角度进入
沈阳这边搞得比较火之后,有朋友把我介绍给当时的广州市委宣传部长、《广州日报》社长的黎元江。他正要创办一份新的都市报《信息时报》。当时是12月了,沈阳是零下二十几度,到了广州是零上二十几度,下飞机以后我简直像是外星人,那一次还中暑了。
当时黎元江就跟我谈,请我过去,给的条件也不错,给一套一百四十多平米的房,老婆孩子的关系也都给解决。但我没直接答应,我说我得回去跟我们老板商量,我总觉得该给张富汉一个交待。
我回去把《广州日报》的事情跟张总说了,他说:“广州那边肯定是个好地方,而且条件又这么高,《华商报》肯定达不到;那你去吧,去了以后,如果有问题你随时可以回来。”
这样我就去广州了,爱人从学校也辞了职,带着小孩一起过去了。举家搬迁。我爱人心也比较细,弄了两个集装箱,连我们家花盆也用集装箱装走了,所有碗筷,一草一木,全部搬过去了。
黎元江号称要拿一个亿来做报纸。我们搞了一个全国巡回招聘,声势搞得比较大。但是没想到,三四个月之内,黎元江就被双规了。于是,我被通知回《广州日报》上班;我不愿意去,就在家里待业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辞职以后,有人在互联网上骂我“报业混蛋”。有次在北京碰见《华商报》第一任总编辑李涛,他给我总结说:张弓惊,你小子,做事情太猛了。那时候年轻,急于建功立业,想用成绩向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回报,也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做事唯恐力度不够,难免照顾不到左邻右舍。我认为李涛总结的有道理。
当时实际上可以回《华商报》,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凤凰卫视,做其所属的《凤凰周刊》。就这样打道回府到西安《华商报》上班,这不是我的性格。当时《凤凰周刊》在深圳上班,我就住在深圳,跟现在《凤凰周刊》的主编师永刚住同一宿舍。在那边事不多,一周就上两三天班,每个周五回广州,周一才过去,工资还给得挺高。我这人耐不得闲,就觉得总想干点活……在那待了三四个月以后觉得这样下去也没意思,又离开凤凰了。
后来又到了好几个地方,有做起来的,也有没做起来的。从那时候开始,我进入报社的角度不止是总编辑或者社长,而已经开始从投资商角度了。
因为熟人介绍,我认识了《公益时报》的社长刘京,并进入了《公益时报》做总编辑。家这时候还在广州的丽江花园,我孤身一人前往北京。就住在三里屯南边白家庄路《公益时报》的办公楼里,风风火火地干。现在这张报纸主办“中国慈善排行榜”,在公益事业圈内小有名气。现在它的LOGO还保留我当时的设计呢。可是由于我当时对公益实在不熟悉,一年左右,就离开《公益时报》。刘社长非常重感情,我离开的时候,召开欢送会,一起吃饭。他虽然为人低调,但的确是个大格局的人,现在各项事业发展都非常不错。
离开《公益时报》后,我去了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做报业投资小组组长。后来这家公司改名为中信文化体育产业集团。这个时候,我开始正式像一个投资商一样看待传媒投资。当时公司总体框架设计非常大,老板一下子想做十几个报纸杂志项目。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能够做起来。
后来又到了云南《生活新报》,这个老板是房地产商,他叫我过去做他所有的一家股份公司的常务副总裁,主管两家报纸,一家是福州的《东南快报》,一家就是昆明的《生活新报》。我觉得在上边做主管太空洞没有意思,就兼做《生活新报》的执行社长。
在《生活新报》,一手抓内容,一手抓发行;最后主抓广告。当时我全家其实已经定居北京了;一个人在昆明。白天开会,抓发行到各个发行站转;晚上,在宿舍支了个传真机,还天天看头版大样。一天上班时间平均18个小时。当时发行推出“订一份报纸送一个小电视”活动,就是那种很小的黑白电视,非常受欢迎。由广东的小工厂生产,一个厂子生产不及,好几个厂子给我加工,每个电视上都有我们的商标,上面打的“生活新报”字样。几个月的时间,《生活新报》一下子火了。
手里有钱了以后,我给报社改善了一下硬件,把报社从昆明有名的“红灯区”(酒吧、歌厅扎堆的地方)搬到一个春城路上比较高档的一个办公楼去,全部实现网络化办公。
但是,我辛辛苦苦装修出来的新办公室,没有坐多久,我就因故离职了。老板当时让我先回厦门休整一段时间,可是我还是直接回北京了。《生活新报》的事业发展此时正如日中天,我就义无反顾地走了。
对于这次离职,我也不埋怨谁。我的解释是:李嘉诚讲过,不要和企业谈恋爱。我更加职业化了。记得我大学刚毕业在广告公司做创意总监的时候,一个创意正做的起劲,客户说:对不起,我们不需要这个创意了,我会说:没关系,你先让我做完。这个时候我已经不会再这样傻了。
回到北京后,多少有点心灰意冷,就希望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前段时间在昆明确实忙坏了。而且,在报业一头扎进去,这么多年了,也确实需要反思一下了。实际上说,说是休息,也没有多长时间,闲不住。然后就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在职研究生。新闻与传播学院崔保国教授对我特别好,和崔老师一起创办紫光传媒公司,我做投资委员会副主任。还参与了他主编的2005、2006年中国传媒产业报告的撰写,后来这两本书都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
继续做投资。和在中信文化做传媒投资的时候认识的一些投资伙伴一起,搞一些传媒项目的投资。和中石化合资做《车友报?星期5》,当时刚从《北京娱乐信报》退下来的崔恩卿做总经理,我做董事兼副总经理。《内蒙古晨报》和太阳晨光传媒公司,也是其中一个项目。
在内蒙古,老百姓本来是没有看报纸的习惯,认为只有开个小生意或者当领导才需要看报纸,普通百姓人家订报纸简直是败家子的行为。我们在内蒙古做了“马上送”社区服务连锁机构,刚开始先招人,拉人头,你这个发行站站长只要你多招人我就奖励你,20个发行站一个站就一两百人,一下子好多人开始订报纸;而且,对老百姓,订一年《内蒙古晨报》送大米和食用油。《内蒙古晨报》一下又火起来了,当地人也开始有了在家里看报纸的习惯。这件事情还被《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过。
看看,这个世界是个心想事成的世界
这些年投资,都算不上成功。股份进进出出,偶尔也参与媒体内部的组织再造。主要是传媒产权的问题,有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在文化产业之内传媒产业之外,也试图做一些其他的项目;这些项目产权相对清晰一些,政策面相对较明朗一些。有一个好处是:做投资之后,离报业第一线远了,但是离钱更近了。投资的单笔收益往往很高,所谓“几年不开张,开张吃几年”。可是,仔细算算,发现做投资这几年挣的钱,如果把通货膨胀算进去,平均起来,和当年在报社每月领工资其实也差不多。
很多时候,你失去一般的,将会得到更好的。这是我多少年来的经验。说“上帝关上一扇窗就会给你开一扇门”,这个是真真实实存在的。面对困难你用这样的心态对待它的时候,你就不会为很多东西焦虑了。
昨天我在我家所在小区的花园里跑步,突然有一个感觉:这个地方我很久以前好像来过。我回忆起来,可能自己在小时候就梦想过和这个场景一模一样的地方,真的梦想过。我跟和我一起跑步的爱人说,你看看,这个世界是个心想事成的世界。
基督教里讲“上帝的引导”,佛家讲“因果”,其实你也可以理解成你下意识里有很多能量。每个人对未来都要有信心,要相信这个能量,就像《圣经》里面说的,如果你有信心,哪怕像一棵芥菜籽那么大的信心,你即使让这座山移去,它也必将移去。
漂泊是你的命运?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中国的报业市场上,悄然出现这样一批人:他们扛着一面用自我的理想和价值编织起来的旗帜,奔走在大江南北残酷激烈的报业市场上,犹如夸父逐日,执着的奔向心目中的太阳。他们自定义为:报业职业经理人。
职业经理人是市场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特殊职业,他们大都“身怀绝技”,站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前沿地带引领着时尚和方向。但是他们基本居无定所,表面看起来命运和未来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实际上完全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和变化。所谓“报业职业经理人”,其实更像一朵朵风雨飘摇的蒲公英,哪里有报纸,哪里就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凭借自己的学历、经历和实力,他们所到之处,必然搅动一场报业战争,在刀光剑影的一番厮杀之后,或成为一方霸主,或黯然偃旗息鼓,转战新的战场。他们是游子,穿梭漂泊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之间;他们是种子,不管成败沉浮,他们的身后,总会有一批年轻的记者像雨后的春草般葳蕤的成长起来。中国的报业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奔波而产生着激烈的震荡,或者干脆重新洗牌。
一切都源于报业的市场化竞争和产业化方向。当资本的欲望和传媒利益的诉求热恋以后,“报纸职业经理人”就呼吸着市场化的气息呱呱坠地。他们认定自己今生就是报纸的孩子,浓烈的新闻情节和对报纸的执着热爱,就是他们血管里奔流的一腔热血。他们生命力旺盛,创造欲望强烈,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一声深情的呼唤,就义无反顾的昂然奔赴,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冲锋陷阵。
但是,现实和理想之间,永远隔着既变幻莫测又难于言说的艰辛历程。人们看到了媒介产生的巨额利润,但是没有看到通向这座“金子塔”的道路上怎样的山重水复、荆棘遍地。
理想只有站在现实的大地上,才可能成就一段传奇或者一个神话。但是“报纸职业经理人”面对的现实却是这样的怪石嶙峋、满目疮痍。社会在转型中,旋转出许多不规则的的裂缝和夹缝。裂缝中,体制和资本的欲望之树迅猛的膨胀碰撞,觥筹交错中勾勒出“双赢和多赢”的壮丽蓝图。“职业经理人”就是他们寻找到的将蓝图变为现实的“超人”。然而,这些“超人”生存在各种力量形成的夹缝中,他们可以滔滔不绝的表白理想和激情,但是,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在这个“职业范围内”,资本说了算、体制说了算,恰好是这些“职业经理人”最没有发言权,最说了不算。
今天种下一棵树,明天就要一片森林!这是许多投资报业的资本普遍的一种心态。准确地说,资本从一开始,不但没有将报纸看作一个需要足够的耐心和宽容的产业,而且因为已经成功者的利润刺激,使它的逐利本性在报业表现的格外的急功近利,而且满带着投机的心态和霸道的主张。市场瞬息万变,体制模棱两可,更为可怕的是资本的出尔反尔。往往,资本最初的财大气粗在市场的第一个回合里就心跳气短,而信誓旦旦的体制在此时总是那样的无能。而且,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任意一个环节出现断裂,资本都不会反省自己,而唯拿“职业经理人”是问:报纸不是一个朝阳产业、暴利行业吗?不是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创造了业界神话吗?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创造这样的神话,或者让神话重现?当这个要求无法以出人意外的速度兑现时,资本初始许下的诺言就变成了“职业经理人”一杯命运的苦咖啡,要么和泪吞下,要么倒掉走人。
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原来的方向和希望,但是“职业经理人”只有扼腕而叹!为了吸引“人才”,开始时,他们都会被许以“优厚的待遇”。现实却是,体制不保障他们的安全,资本不保障他们的利益。他们永远都是体制外的人,永远都是资本的“打工仔”甚或奴隶。就像蒲公英一样,“漂泊,是你的命运”!他们充满遐想又不知所往,他们激情澎湃但是躁动不安,壮怀激烈但是惆怅万端。千回百折中,他们历尽磨难,却距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遥远。
原来,一个“报业职业经理人”,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张“信息纸”,更多的时候,要面对和应付的是体制、资本、市场的多层挤压和逼迫,他们是在刀尖上舞蹈,夹缝里讨生活。他们要对市场负责任、对资本负责任、对体制负责任,唯独没有人对自己负责任!所以,一张报纸可以在4年内换11任总编,而一位“报业职业经理人”可以在6年内换十几家媒体。不停的断裂、不断的失意,于是就注定了“职业经理人”不息的奔走。没有归宿感是他们所有人都无法摆脱的心中的隐痛。当他们明白这一切,却已经晚了,一切都成了过去。这种走马灯似的轮换中,报纸被折磨的乖戾而且畸形,而职业人则常常是伤痕累累,两手空空。
现实还是这样的现实,理想却已经不是那个理想。种下的是血汗,收获的却是伤痛。报纸“职业经理人”的“职业”历程中,更多的是疲惫的身影和传奇般的故事,没有大地丰收的喜悦和累累的果实!
当然,不能都是体制和资本的错,相比较于其他的“职业经理人”,报业的“经理人“群体还是太稚嫩了、太粗糙了。报纸的经营管理和与资本的合作,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门全新的课程,而且越来越变成一种群体的理性行动,最起码,已经不是个人心血来潮时的一时冲动。但是,报业年轻的“职业经理人”们没有什么“资格证”,没有一个专业化的权威的机构给他们的能力和资格进行包装和认定。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体系”,甚至自己的利益遭到侵害时,连一个维权的地方都找不到。包括他们自己,至今都没有像真正的职业经理人那样对即将奔赴的市场首先进行科学系统的,具有量化标准的调查和分析。凭着报业理想,燃烧起来的炽烈激情和欲望,精英式的气概和承诺便掩盖了对于报业市场的理性认知遑论,专业化的深入调研和剖析。只是凭借着感觉、经验甚至是一段和报纸没有关系的友情就决定了一个行动!当然,传统知识分子的简单理想化和迂腐的偏执清高,也是“报纸职业经理人”浑然不知的一个硬伤,他们将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互相的“不配合、不低头”看成是一种“骨气”,但常常是这种骨气伤害了多方的利益,使一个“花好月圆”的开始最终在“四分五裂”中结局。如果真是这样,就实在怨不得别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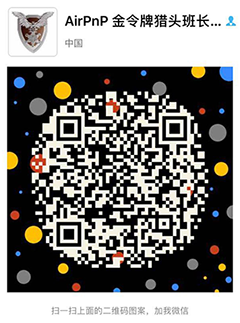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0160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01605号